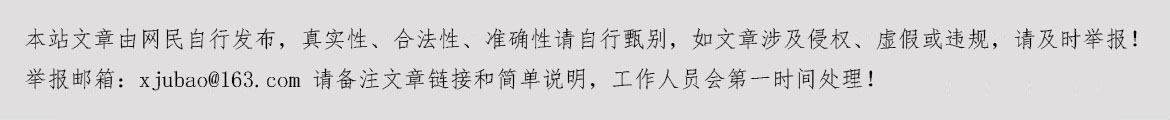1985年初,开国大将陈赓的夫人傅涯赴美公务并探亲,此时正在美国的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等得知消息后,纷纷热情款待。
访美结束后,傅涯欲搭乘飞机回国,正要上飞机时,宋希濂猛然抓住她的手,将一把钱塞进她手里道:“请你回国后,代我买些鲜花和纸钱,告诉他,我在这边一切安好!”说完后,宋希濂眼里已经满是热泪了。
傅涯见到这些钱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待她完全反应过来时,宋希濂已经迈着蹒跚的步子走远了,那一刻,傅涯的眼框也湿润了。
这一年,宋希濂年已78岁,此时,距离陈赓辞世,也已经过去了近20年。是怎样的情义,让宋希濂如此念念不忘呢?这个问题的答案,得从他们初识那年说起——
1923年,即民国12年,孙中山在痛定思痛后决定创办革命者自己的武装。随即,孙中山派人前往湖南长沙招募优秀学子。得知消息后,无数湖南有志青年纷至沓来。这群青年中,便有时年20岁的陈赓和年16岁的宋希濂。
陈赓与宋希濂
当时的陈赓和宋希濂都还是学生,陈赓正就读于岳乡中学,而宋希濂则就读于长郡中学。去长沙报考的路上偶遇后,两人发现:他们不仅年纪相仿,而且还同是湖南湘乡人,还都对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见解一致。
更为重要的是,他们发现:两人此行,竟都是为了前往长沙考试。
那一路,两个年轻小伙越聊越投机,颇有“相见恨晚”之感。也从相识那天起,内向的宋希濂便喜欢上了陈赓的笑,每次他笑时,他总忍不住跟着呵呵笑。
当年初冬的一个上午,长沙市育才中学的考场上,陈赓惊奇地发现:他的同桌竟是前段刚刚认识的宋希濂。宋希濂看到和自己并排坐的正是陈赓后,也惊讶极了。
这次考场相遇,更加增进了两人的友谊。6天后发榜,两人同时被录取了。那一刻,两人都喜不自胜。
当时,从湖南招募的100多名学生,都绕道进入了广州,他们的大部分都进入了程潜办的讲武学堂。
陈赓和宋希濂都非常机灵,他们到广州后第一时间打探了情况。他们得知:孙中山先生已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,他已决定在广州创立黄埔军校,培养革命军事人才。
无疑,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!随后,两人相约到军校筹备处打听招生条件和招生日期,3月中旬,两人同时报了名。
不久后,两人在中山大学参加了考试。在2000多名考生中,这对来自湖南湘乡的青年双双以优异成绩被录取。
1924年5月5日,意气风发的两人乘船到了黄埔军校。从此时起,两人都光荣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。
入军校后,陈赓被编在了3队,而宋希濂则被编在了10队。在这所国共合作共创的军校里,两人的友谊进一步加深。
每次在军校碰面时,陈赓总是笑着快步向他走来,然后,两人会“勾肩搭背”地一道走一道闲话。也因此,后来的几十年里,只要回忆起黄埔军校,宋希濂脑子里便会浮现出陈赓笑着走向他的画面。
在黄埔学习的日子,无疑是宋希濂一生最珍贵的回忆。当时的黄埔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,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,虽是阵线鲜明的两大营垒。但本质上,他们方向一致:都是为救国救民。
黄埔军校校门
陈赓早在1922年便经由长沙育才中学进步教师熊亨瀚介绍,加入中国共产党,他担任了3队共产党的支部书记。
结识宋希濂后,陈赓便一直寻思着介绍他入党。
最初,性格内向的宋希濂在两派中,一直不偏不倚。可随着与陈赓交往的加深,他开始倾向于共产党,并积极参加左派的一些活动。
军校学习期间,宋希濂一直格外关注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,他还知道:陈赓与周恩来来往密切。
1924年8月,周恩来第一次在大花厅演讲,当日他的演讲主题是《国内外形势》。因为有事,宋希濂去晚了,所以去时他离演讲台很远。
为了能听得清且亲眼看看这位周恩来主任,宋希濂于是便拱一下,挪一步,慢慢往前挤。挪着挪着,挤着挤着,他正巧遇上了陈赓。见陈赓两眼放光地听着,他也靠着他,出神地听着。
那场演讲真是精彩啊,宋希濂记得,人群中每隔一会儿,就会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。一次鼓掌的当口,陈赓凑到宋希濂耳边道:“怎么样?周主任是个栋梁之材吧!”
“当然,当然,而且是年轻的栋梁之材,漂亮的后起之秀!”宋希濂连连点头,脱口而出。
听完演讲后,两人都发现:他们的手掌都拍红了。
正是这次演讲后,敏感的陈赓发现了宋希濂对周恩来的敬佩。为了帮助这个好友接近他钦佩的人,他决心带着好友亲自面见周恩来,以让他聆听周主任的教诲。但因为种种原因,这件事情一直未能如愿。
军校期间,除了周恩来外,最让宋希濂佩服的便是他这位好友陈赓了。陈赓为人豪爽、性情坦率,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且多才多艺。因为敬重陈赓,宋希濂只要得空便和这位老乡在一起谈论学习、国事。
在陈赓的影响下,宋希濂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。
陈赓他们就读的黄埔军校成立于危难之际,也因此,陈赓等第一批学员在军校学习仅仅半年后,便迫于形势,拿起枪杆直接投入了平定广东各路军阀的战斗。
陈炯明叛军被平叛后,陈赓与宋希濂返回广州,他们先后被提拔为了连长。正是在此期间,陈赓因为二次东征时救了蒋介石一命,曾被调任为蒋介石侍从参谋。陈赓对此并无太大感觉,但很快,因为发现蒋介石掩藏在革命面纱下的反动本质,他毅然以母病为由离开了蒋介石。
正是东征这年,陈赓介绍宋希濂入了党,对这个小自己三四岁的小老乡,他寄予了厚望。
宋希濂
回到广州后,陈赓与宋希濂的交往更加密切了。陈赓是个心细如发的人,他一直惦记着此前心里想的事:让宋希濂面见自己钦佩的周恩来主任。为了这次引荐,陈赓可没少花功夫。
一切准备就绪后,陈赓便决定给宋希濂“惊喜”了。
那日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陈赓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。他事先并未告诉宋希濂要去见谁,只说:“我要带你面见一个要人。”
宋希濂听了自然好奇,于是他一次又一次盘问到底是谁,可陈赓却始终笑而不答,见此情景,宋希濂心里更加好奇了。
说来,陈赓也当真会卖关子,他当日竟把宋希濂带到了大兴公司附近一幢房子的二楼。两人推门而入后,一脸好奇的宋希濂一眼便认出了坐在写字台前的主人竟是周恩来。那一刻,他整个人都怔住了。反应过来后,他立即收拢脚跟,挺直身子,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道:“报告周主任!”
周恩来满脸笑容地和他们一一握手,并请他们坐下。可宋希濂却很紧张,他坚持站在原地继续道:
“报告周主任,我叫宋希濂,是教导二团第四连连长。陈赓是我的同学和同乡,他约我进城面见要人,但没有告诉我见……”
周恩来听了笑笑道:“哈哈,陈赓又卖关子了。”随后,他让宋希濂坐下并笑着说:
“你不必报告了,陈赓早就同我讲过了。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,这很好嘛!中国革命的重担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肩上。你们是我的学生和部下,也是我的同志,不要拘束,随便谈谈。”
周恩来
宋希濂听到这话后,平静了很多。那日,他们三人聊了很多。当聊到对革命形势的看法时,宋希濂和陈赓出现了分歧。
宋希濂对革命形势颇为乐观,他认为:“国民革命的道路已经打通,革命胜利之日为时不远。”陈赓却认为:“虽然当前革命形势发展很快,工农群众已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,但整个国民革命任重道远,今后也难说是一帆风顺。”
从周主任处出来后,宋希濂埋怨陈赓没让他做准备,可陈赓却嘿嘿笑着说:“老弟,这意外的见面,不是印象更深刻一些吗?”
陈赓说准了,几十年后,宋希濂依旧记得这次见面时的情景,他甚至对当时三人的谈话内容也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日陈赓明媚的笑脸和爽朗的笑声,也永远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。
就在这之后不久,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宋希濂因辨不清方向,而私下给陈赓写信,信里,他说自己常常:“云雾重叠,风向不辨不知如何是好?”
宋希濂之所以辨不清方向,是因为当时的他正面临着选择。
一方面,他已加入共产党;可另一方面,中山舰事件后,蒋介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、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大权。于是,认定只有获得蒋介石青睐、才可以顺利升迁的宋希濂,动了加入国民党的心思。
实际上,给陈赓写信时,宋希濂已经做出了选择:只要蒋介石抛出橄榄枝,他便会倒向国民党。
陈赓已经意识到宋希濂有了摇摆,但当时他太忙了。因为忙于战争,接到宋希濂书信后,他一直在找空挡回信。
中为陈赓
让陈赓没想到的是,没等他回信,宋希濂便被调往广州。之后,跟着蒋介石的他,被提升为了营长。
被提拔后,宋希濂心里高兴极了,他甚至开始怪自己“何必当初”。后来的回忆中,他曾对自己当时这种心态进行过详细描述。
此时的宋希濂眼里,昔日让他敬重的学长陈赓反而成了“麻烦”了,他一直寻思着怎么跟陈赓说明。思来想去后,宋希濂决定给当时同在广州的陈赓再次写信。可这信怎么写呢?正在他苦思冥想之时,陈赓却先于他写信约他见面了。
宋希濂此时是真不想再见陈赓,可因为往日的情分,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。
陈赓约的见面地点是一个僻静处,抵达后,两人在一棵大树旁坐下了。坐定后,陈赓郑重地发问:“你为什么几个月没有同组织上联系?你在部队做了跨党登记没有?”
宋希濂见陈赓一脸严肃,他感觉到自己只能说实话了,他于是沉思了一会后道:
“我在潮州还没有来得及作跨党登记,就调到新编二十一师,现在这个部队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,还用得着自找麻烦,去登记吗?”
陈赓听到这儿脸色大变,那一刻,他对这个曾被自己寄予厚望的老弟失望透顶了。一股莫名的气愤涌了上来,他是真的“恨铁不成钢”啊,可他知道:这时候不是发怒的时候。定了定神后,他决定用心平气和的方式和他沟通,他平静地说:“我希望你开诚布公,谈谈自己的真实想法。”
宋希濂听到这儿,知道自己不把想法说出来是过不了关了,他鼓足勇气道:“我认为,当今中国,哪个党派不重要,重要的是目标一致。我打算不再跨党,但我保证绝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!”
陈赓认真听完后继续问道:“如果有一天,风云突变,国共不合作了,两军对垒,你站在哪一边,为谁以身殉职,听谁的军令?”宋希濂知道这个回答一出口便会伤到陈赓,所以他选择了把问题踢回去,他于是说:“眼下广东局面很好,我不明白你的假设从何说起?”
陈赓知道,自己若一味再坚持做工作,可能会适得其反,他于是耐着性子说了最后一句话:
“我们都冷静一下,认真地想一想,可能有好处。我希望我们再见面,也可以先通信,好不好?”
这次谈话后,宋希濂可能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,毕竟他自己是“背离者”。聊完天的当晚,宋希濂总觉得他们这次聊天有些异样。想了半天后,他总算想明白了:这是陈赓和自己认识这么久,第一次全程没有笑脸。
宋希濂与陈赓
几天后,宋希濂给陈赓写了一封长信。
陈赓收到长信后,未来得及再次与老友见面,便奉命调离了广州。离开前,他匆匆忙忙给宋希濂写了一封长信。
当时的两人都并不知道:这一别,将是十年。十年间,两人一直互相关注着对方。
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期间,已脱离共产党的宋希濂正因腿伤在苏州教会医院治疗。住院期间,宋希濂再次想到了自己的未来。此时,已经到了昔日陈赓与他聊天时提及的:“真正抉择”的时候。
在十字路口,宋希濂有过犹豫。但最终,他再次选择了蒋介石。宋希濂觉得:蒋介石是个手眼通天的人,跟着他绝对没错。
这样想了以后,宋希濂决定试探性地给蒋介石写一封信。
可信寄出去后,他先收到的,竟是老友陈赓的信。看到信后,宋希濂很感动,他知道陈赓一直关心着他,陈赓甚至让他迅速来武汉养伤。
陈赓的信,让宋希濂一度陷入了激烈的矛盾中。可想来想去,他还是决定“先看看蒋介石的答复再说”。
几天后,一位青年军官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到了宋希濂的病房,蒋介石在信里写的是:让他病愈后速去南京。蒋介石还随信附赠了300大洋的“路费”……
仅仅三天后,宋希濂便毕恭毕敬地出现在了蒋介石面前。这也意味着,宋希濂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。从此,他的半生就拴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,开始了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。也因此,十年间,他和陈赓唯一一次可能的见面机会就此被错过。
陈赓与蒋介石
但分别时的十年间,两人一直互相打听着对方的消息,他们也常有交集。两人最大的一次一次“交集”,发生在陈赓被捕时。
1933年,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陈赓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,他当时被关押在老闸巡捕房。
陈赓被关押的消息迅速传到宋希濂耳中,宋希濂这次真着急了,跟了蒋介石这么多年,他深知:陈赓这次凶多吉少。
关键时刻,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展开了营救。宋庆龄甚至还直接跑到蒋介石面前“提醒”他:陈赓曾救过你的命!
这一切的动向,宋希濂都看在了眼里,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与陈赓有关的所有消息。他曾寄希望于陈赓能接受蒋介石的劝降,那样他们俩又可以在同一个战壕了。
可陈赓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何等坚定!他岂会接受蒋介石的劝降?眼见陈赓迟迟没有被释放的可能,宋希濂便联合黄埔一期的同学肖赞育、项传远、宣铁吾等十人,联合签名请求蒋介石释放陈赓。
前排右三为宋希濂
之后不久,蒋介石终于将陈赓从牢里放出软禁在了客房,并给予了较多自由。这样一来,陈赓便有了逃跑的机会。陈赓逃脱后,宋希濂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事后,蒋介石曾将宋希濂痛骂了一顿,但也仅此而已。
距离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十年后,西安事变爆发。此时,年已30岁的宋希濂已扶摇直上出任二十六师师长。事变发生时,他正任西安警备司令。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。1937年4月,年34岁的陈赓由延安来到西安。十年未见的两人,终于再次走到了一起。
十年间,昔日的少年都已不再。可宋希濂却发现:陈赓的笑脸始终未变。他笑起来,仍会露出八颗牙。而陈赓也发现,昔日那个内向的少年,依旧会不自主地显出羞涩。
这次相聚,两人边喝边聊,似乎有说不完的话。推杯换盏间,两人都看到了彼此眼里的泪。他们比谁都清楚,在这个年代里,分属不同阵营的他们,能一直保留着情谊,是多么珍贵。
转眼,十二年过去了。十二年间,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经过几番较量,蒋家王朝已土崩瓦解。
1949年,宋希濂在四川省峨边县的沙坪被俘。随后,他被关押在了重庆石磁口的白公馆。这一年,宋希濂年已42岁。
被关押期间,宋希濂极其沮丧。他心想着:反正自己是失败者,生死听便。囚禁期间的宋希濂把自己当“行尸走肉”,他每日的生活总结起来便是:"夜里望天亮,早上望吃饭,中午望晚饭,吃饭望睡觉。"
囚禁生涯,是宋希濂这二十多年第一次真正“闲下来”。人一闲下来,总免不了回想往事,回想中,宋希濂除了想起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、妻子外,最常想起的人,便是军校的同窗陈赓了。
宋希濂再次想到了提笔给陈赓写信,可一想到此时人家已是声名显赫的解放军兵团长了,而自己却是阶下囚,他的笔便重得让他提不起来了。几番折腾后,宋希濂终于放弃了给陈赓写信。
宋希濂做梦也没想到,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给陈赓写信时,陈赓竟从繁忙的军务中抽空,专程从云南边陲赶到了重庆。
在那般情境下看到昔日的故友,宋希濂终于在握住陈赓手的瞬间落泪了。陈赓也努力克制着自己情绪,他紧紧握着宋希濂的手道:“看见你身体不错,我很高兴!”
说完这见面的第一句话后,陈赓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了,他调整了下情绪接着道:“我们最后见面是什么时候?”
陈赓的一句话,直接把宋希濂拉回到了十二年前。那时,他们都是师长,他在西安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陈赓,那时,他们真年轻啊!
“西安事变后,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找我。”宋希濂一边拭泪一边回答道。陈赓赶紧接着道:“对了!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去拜访你的,你还记得哩!我们当时能见上,要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呢!”
那日,两人手拉手聊了很久,他们的谈话,一直从上午10时持续到了下午4时。谈笑风生间,两人似乎又回到了黄埔时期。
临别前,陈赓为宋希濂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和途径,他还嘱咐他不要有任何精神负担。陈赓的话,如春风般抚慰了宋希濂。此后,重燃希望的宋希濂开始看书、学习,他对共产党的疑虑也随之被扫除了。
之后,有了思想觉悟的他,甚至开始写回忆录。
重庆生活两年后,宋希濂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他经常与杜聿明、范汉杰、王耀武、黄维等许多老同学、老同事重逢,并生活、学习、劳动在一起。
宋希濂竟慢慢地被养胖了,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好了,党和政府也加速了对他们的思想改造。宋希濂有时候觉得,自己被关押期间学习的,恰恰是当年没有跟着陈赓一起学完的部分。
1956年,是宋希濂被关押的第七年,这一年也是他收获最大的一年。正是在这年,他确确实实地认识到:自己曾怀着救国救民的思想,干过不少错事。其中,杀害革命党人瞿秋白便是其中之一。
宋希濂之所以能认识到自己曾干过“错事”,多少因为他终于看到了新中国的真实面貌。当年5月,他和同伴们被邀请去天安门参加了一场庆典。
庆典上,宋希濂看到的无数洋溢着幸福的笑脸,当他看到长达十里的长安街,加上天安门广场,都已变成了人和旗帜的海洋,且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时,他才真正意识到:只有共产党,才能救中国!
当天的日记里,他激动地写道:
“参加这个盛会的到底有多少人?五十万?一百万?恐怕难以准确计算……欢乐,真正的欢乐,发自内心的欢乐!为什么?因为劳动人民当了家,做了主,在欢庆自己的节日。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,新中国成立六年来取得辉煌的成就!”
写下这段话时,宋希濂的眼里噙满了热泪,他不禁感叹:“没有剥削,没有压迫,不就是现在这般么!黑暗的旧中国终结了,新中国升起了……”
可以说,1956年确实成为宋希濂新生之路的转折点。越是认识到共产主义的正确性,他对陈赓也越发充满感恩了。与此同时,愧疚等等复杂的情感也在他心里升腾起来。
陈赓与家人合影
当年,他在自己写的《一九五六年学习总结》中惭愧地写道:
“像我这样的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,榜上有名的战争罪犯,共产党不杀我,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。”
正是在认识到自己曾犯下过大错期间,本来因为有陈赓的开导而心存希望的宋希濂,再次心灰意冷了,他觉得自己的前途很渺茫,他曾感叹道:
“我始终觉得渺茫,觉得不能恢复自由,新社会再好,对自己意义不大,前途仍是暗淡的……陷于苦闷烦躁之中……”
最难熬的时候,宋希濂再次想到了陈赓,他经常靠回想老友昔日勉励的话来支撑自己。宋希濂并不知道:因为长期处于紧张工作和战斗中,陈赓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,他被囚禁期间,陈赓经常受疾病的折磨。
陈赓与粟裕
1959年,被囚禁十年后的宋希濂因表现突出,成为首批特赦释放的三十多名战犯之一:他自由了。
恢复自由后不久,陈赓在四川饭店摆了一桌酒席,约请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郑洞国等黄埔同学小酌。再见宋希濂时,两人紧紧相拥时,他的第一句话便是:“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。”
那场聚会持续了数个小时,期间,他们再次推杯换盏,陈赓的笑声依旧爽朗。宋希濂甚至恍悟:他还是昔日的少年陈赓。但他并不知道:当时陈赓的病情已经很重了。
那次聚会时,陈赓详细询问了宋希濂的生活,对于老友将来的一切,他终于放下心了。这次聚会后,周总理又亲自安排了一场宴席。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时,宋希濂感慨万千,往事也一幕幕在脑海中重现了。
前排左二为周恩来;左三为陈赓;后排右一为宋希濂
宴席后,陈赓与宋希濂单独照了一张像,之后,他们愉快地一起沿湖散步。宋希濂并未察觉到:此时依旧爽朗笑着的老友,即将走到生命尽头。
1961年3月16日,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辞世,享年58岁。惊闻噩耗后,宋希濂悲痛万分。陈赓的葬礼上,他哭得像个孩子。
后来,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
“陈赓逝世是国家的一个巨大损失,对于我个人来说,也是丧失了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友。他的伟大,他的忠诚,他的卓越指挥,他的无私无畏……都是我永远不能忘怀。”
如陈赓所说,自由后的宋希濂迎来了他的“好日子”。也是在自由后,他终于走上了新路,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。宋希濂在满怀感恩的同时,也暗暗发誓:要把自己的余热,发挥到为国做贡献上。
此后余生,宋希濂将毕生精力放在了祖国统一大业上,凡是对国家统一有利的事,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。即便后来到了美国养老,他也始终惦记着祖国强大统一。
可以说: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里,宋希濂终于完全和老友陈赓站在了一起!这,也成了宋希濂余生的最大欣慰。
中为晚年宋希濂
宋希濂在美国的日子里,最常想起的依旧是陈赓。也奇怪,越是年岁渐老,他记忆中的少年陈赓的形象竟反而越发清晰了。他记忆里的少年陈赓,总是笑着的,那笑容,一如春风抚慰着他……
如果世人问宋希濂:人生得一知己,足矣?他的答案定然是:人生得一知己,足矣!